|
|
|
到梵林墩去的人
原價:
HK$12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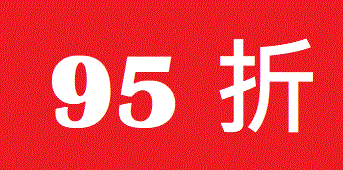
現售:
HK$120.65
節省:
HK$6.35 購買此書 10本或以上 9折, 60本或以上 8折
抱歉! 此商品已售罄, 不能訂購
|
| |
|
|
| |
|
|
出版社: |
聯合文學
|
| 出版日期: |
2019/05/22 |
| 頁數: |
312 |
| 尺寸: |
14.8x21 |
| ISBN: |
9789863233039 |
|
|
商品簡介 |
你不該躲在屋角裡一個人哭,
年輕人該到梵林墩去。
沒有甚麼地方的風像梵林墩的那樣柔……
尉天驄╱短篇小說集
▌尋覓種種掃除陳腐、一新耳目
足以誠實表達心情的實驗風格
諸如海明威《老人與海》文字的簡淨與孤寂、貝克特《等待果陀》劇場中前言不對後語的荒謬,又或如雷奈電影《廣島之戀》中不同時空的夢幻交疊……這些受戰後存在主義影響的西方藝術風貌,同時帶動了台灣一代新文藝的各種實驗。從尉大哥的小說裡,便也可以看到一份「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浪遊和尋索。——奚淞
▌我的年輕時代所體驗的種種,
也許就是這個時代的一些面影吧
一個人只有面臨某種困境,才能體認出羅曼蒂克的情緒的蒼白,只有面對自己的弱點,才能撕去自身的「偽裝」……我們寫作,把作品聚在一起,讓它像一面鏡子照出我們的弱點,一方面也投入世界去作為彼此間的交通。——尉天驄
▌年輕人:「人最可悲的是對自己沒有了自由」
一部充滿實驗性、高度象徵,飽含韌性與氣氛的作品
十三個短篇故事,分別來自作者三個階段的小說成就:開首五篇〈母親〉、〈內陸河〉、〈匍匐之秋〉等描繪主人翁忽明忽滅的心理狀態,是最純粹的現代主義文學創作;中段〈大山〉、〈到梵林墩去的人〉到〈艾玲達!艾玲達!〉諸篇則是個人風格代表作系列,大量的對白敷演現代人的心靈風暴;在表面看似「虛無、蒼白、病態」的美學意境之下,實則跳動著對「生命、愛情、自由」勇於探索的年輕心靈。
與前此大不同的壓卷作〈唐倩回台灣〉,獨具議題性,見證當年文學運動風潮歷變後,一代知識分子們對自身理念與任務的反省。
特別收錄
‧著名劇作家姚一葦論〈到梵林墩去的人〉,為其少數對小說作品之重要評論。
‧散文名家王鼎鈞特寫〈被殺者〉的結局發展,堪為短篇創作的觀摩範例。
‧廖任彰專論《尉天驄與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節錄,深度分析創作理路。
作者簡介
尉天驄
作家、文學評論家、政大中文系名譽教授。
一九三五年生,原籍江蘇碭山,一九四九年隨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來台,政大中文系畢業;勤於教學、讀書、寫作,定居台北木柵至今。
一九五九年五月四日,尉天驄自王藍、陳紀瀅手中接辦《筆匯》雜誌,標明「革新號」,與過去黨國色彩切割,強調青年人為主體,引介西潮,擴展在地視野。《筆匯》停刊後,一九六六年創辦《文學季刊》,姚一葦、王禎和、劉大任、黃春明、王拓、七等生、陳映真、施叔青均為該刊重要撰稿人;堪稱「台灣鄉土文學的源頭」,對台灣文學的發展影響巨大。該刊接續於一九七一年轉型為《文學双月刊》,一九七三年改名《文季》季刊等系列;自五○至八○年代,尉天驄傾力興辦雜誌、主持編務,卓然為台灣文壇的拓荒者與傳播者。
曾獲:巫永福評論獎,兩屆金鼎獎文學圖書獎,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貢獻獎。
著作:評論集《文學札記》、《路不是一個人走得出來的》、《民族與鄉土》、《鄉土文學討論集》(編著);小說集《到梵林墩去的人》;散文集《天窗集》、《眾神》、《理想的追尋》、《棗與石榴》、《回首我們的時代》;學思歷程回顧《荊棘中的探索:我的讀書札記》等。
書籍目錄
【序】
心靈的召喚與浪遊——重讀尉大哥青年時代的短篇小說集《到梵林墩去的人》╱奚淞
母親
內陸河
匍匐之秋
變調的玫瑰
微雨
大山
到梵林墩去的人
大白牙
被殺者
5點27分
又一個晴朗的日子
艾玲達!艾玲達!
唐倩回台灣
【評】
論〈到梵林墩去的人〉╱姚一葦
遺恨:〈被殺者〉結局透視╱王鼎鈞
【附】
談《到梵林墩去的人》:尉天驄現代主義小說之評論╱廖任彰
推薦序/導讀/自序
序
心靈的召喚與浪遊 ╱奚淞
近年尉天驄出的書都是相關台灣近代文學、重量級的好書。二○一一年《回首我們的時代》,生動描繪一系列文藝創作者的肖像。二○一四年《荊棘中的探索》,天驄大哥以個人讀書札記風格,呈現劇烈時代變動中,作者不畏橫逆、以知識分子堅定的思考和書寫,銜接戰後文化斷層,為文藝開啟新局的心路歷程。
本來滿心期待天驄大哥會步入更豐盛的寫作期,然而就在《荊》書出版後不久,驚聞大哥遭遇車禍,傷及脊椎中樞,從此不便行動,僅能以輪椅代步,臥床至今已近五年了。不久前,「聯合文學出版社」的總編周昭翡告訴我,準備重新收集、整理尉大哥早年刊登在《筆匯》革新版及《文學季刊》中的短篇小說出版。這消息真令人高興。想到一甲子前,就在台灣被稱作「文化沙漠」的時代裡,大哥支撐《筆匯》並創刊《文學季刊》及《文季季刊》,在這片沙漠中辛勤灌溉、培育並庇護星點綠苗;不少當年呈初生態的創作,今日已成備受矚目、見證近代文學史的重要作品;相對之下,大哥早年那些充滿實驗性的短篇小說,是被掩蓋在他作為早期文學園地拓荒者的身份下而少有人欣賞並研究了。
我翻尋書架,終於找到大哥送我、他珍貴的第一本小說集——一九七○年由「大林文庫」出版、共收錄八篇小說,並以其中一篇為書名的《到梵林墩去的人》。
即使相隔半世紀,重讀尉大哥青年時代的作品,並不覺得遙遠、陌生。晚上床頭挑燈夜讀,逐篇逐句,當年覺得神祕之處依然顯得迷離;曾經會心之處仍舊令我微笑而感動。
當我讀到那篇〈艾玲達!艾玲達!〉小說末段,文中描述那彷彿發自主角幻聽、從都市夜空彼端黃昏星遙遙傳來「艾玲達」的呼喚……我不禁惘然放下書本,閉目冥想當時年輕英挺的尉大哥,心中懷著何等飄忽如夢的情懷?
有一次我問尉大哥:「為甚麼你小說中的年輕人堅持要去那連地名也不存在的『梵林墩』?『艾玲達』是真實人物嗎、這名字又在叫喚誰?」大哥只是笑,像身懷藏寶地圖,不肯示人。我於是逕自參詳這段文學公案,唸出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所說的人生三境界,看看能否契合尉大哥的心路歷程: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界也……」
天驄大哥聽了,抿嘴點頭。這就對了罷?!
王國維以三段詞句,描寫個人生命的浪遊、苦澀追尋,乃至於究竟歸宿。其實它道盡今古,在人性上,哪有古典文學和現代主義流派的分隔?
創作〈到梵林墩去的人〉系列小說時,三十歲上下的尉大哥真個是「衣帶漸寬終不悔」,浪遊在剛引進台灣的現代西方文藝潮流中、尋覓種種掃除陳腐、一新耳目,足以誠實表達心情的實驗風格,諸如海明威《老人與海》文字的簡淨與孤寂、貝克特《等待果陀》劇場中前言不對後語的荒謬,又或如雷奈電影《廣島之戀》中不同時空的夢幻交疊……這些受戰後存在主義影響的西方藝術風貌,同時帶動了台灣一代新文藝的各種實驗。從尉大哥的小說裡,便也可以看到一份「為伊消得人憔悴」的浪遊和尋索。
不能忽略了那仍是處在台灣漫長軍事戒嚴、白色恐怖壓力下的年代。日後,作為帶動並參與當年文藝風潮者的尉大哥,曾為被批評為「虛無、蒼白、病態」的現代詩和小說作過辯解。在那段強權當道、思想受壓制、傳統朽敗的時代,該用什麼方式才能揭開籠罩四周的謊言和悶局?當年的現代主義即使顯得蒼白、虛無,也不失為坦露真心的利器,為苦悶時代劃出一道透光裂隙。
一九七○年出版《到梵林墩去的人》,天驄大哥在自己第一本小說創作集的〈後記〉這麼說:
……在這部書的作品裡,我所領受的卻是一種死亡和一種重生。因此,如果有人在這些不成熟的作品裡感到一些虛無的氣息,我盼望他們僅把它當作一種生命成長的過程……我願用這個集子作為對過去的告別!
告別不代表消失。尉大哥隨歲月繼續「眾裡尋他千百度」的探索。我心目中的尉大哥,一直是全方位的生命關懷者;他不只是文學家,也始終是學不厭、教不倦的文化思想傳道師。從《荊棘中的探索》一書,足可見大哥對文明承續和人類前途的關懷和用功,真的是「尋他千百度」也不厭倦。
自二○一四年七月大哥遭車禍之災,關心的朋友和學生絡繹不絕,他的病成了大夥共同的懸念。今年前後,我多次探望臥床的尉大哥。每次去他家之前,總不免懷一份忐忑心情,擔心他久病的身體和情緒。然而,事實上,對於大哥脊椎受傷後的處境,凡是探視過他的朋友都會說:「從未見過如此頭腦清楚、記憶力驚人、正面思考的病人。」我每次探望過後,心中也都多一份清明,覺得大哥仍然在生活中提攜、敦促著我。
在桂芳帶著印傭安妮的悉心照料下,大哥的日常生活很規律,例如:晨起拉筋、早餐,以輪椅代步往附近政大校園散步。歸來後小睡後,或可接待訪客、或可以坐桌前寫毛筆字。雖然因為久臥手腕僵化以及久患痛風,大哥執筆並不方便,但他仍堅持以他特殊的捉筆方式,書寫他記憶裡的古今詩文……
「允晨文化」的廖志峰,曾在一篇〈早秋〉文中,描述探病時天驄大哥有點孩子氣撒嬌式的抱怨:「寫字,握筆握得手好痛。」當時可以見到客廳周遭貼牆的大書櫃上,懸著一幅幅長條宣紙書法。由於病體不靈活的運筆落墨,書法顯得十分樸拙、有如斧鑿刀刻,字字如拳,卻蒼古渾厚。
因為欣賞到大哥書寫漢高祖的「大風起兮,雲飛揚」渾雄有勁的句子,志峰離開天驄大哥家後,興致高昂的他不願即刻搭車離去,在晴好的秋光天色中,沿秀明路走了好長一段路。
探望尉大哥,說是探病,卻也能增益見聞甚或療癒了自己的心病。「聯合文學」的昭翡,在「歧路花園」專欄中的一篇散文中寫到她自希臘旅行歸來後,赴秀明路看尉大哥。大哥在床上高興道:「希臘,好呀!」話題便由希臘延伸到英國詩人拜倫的長詩〈哀希臘〉,又談起民國初年翻譯拜倫作品、「情僧」蘇曼殊一生的浪漫事蹟。「知識之樹,終非生命之樹。」昭翡在散文結語中,如是讚嘆尉大哥:
「……有關文學,必須化生命為體驗。尉老師就像一株生命之樹。儘管不能像往常一般自由移動,但思想卻如此活潑,以其生命的歷練,不斷給我帶來滋養與啟示。」
今年舊曆年前偕畫家黃銘昌訪尉大哥時,為大哥窗上貼上我親手剪的新年剪紙,乘機貪心的向大哥討了他最近寫的書法。
黃銘昌得到的是《三國演義》裡的孔明詩句:「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
我則得到詩佛王維的詩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多好的句子!在生命每個拐角,總能遇上它;這便也就是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形容人生境界的結尾,所謂「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意境了。
四月裡櫻花飄飛、桃李盛開。我奉昭翡之邀,特為尉大哥即將出版的小說集寫幾句導讀——以大哥人生與文學歷練的豐富,哪容得上我這做弟弟的說話?便還得銜命往訪秀明路、探望尉大哥,或可啟發一些靈感。
「……寫小說,大哥心裡可是藏著初戀愛人的名字嗎?」我又一次執拗地追問起小說裡「艾玲達」的象徵意義了。臥床枕頭上,八十四歲尉大哥的容顏和悅、眼神帶一份調皮,忽然從言語中流淌出似乎久違、又十分鮮明的詩句來,大哥吟詠:「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我本能反應地接口道出五言詩的下兩句:「——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
「你知道這是誰的詩?」大哥考問。我傻楞楞回答:「不知道。」
「呵呵,」大哥笑著說:「裴多菲,十八世紀匈牙利詩人。」啊,便是那位以長劍和鵝毛筆,為抵抗奧君、保衛祖國而慷慨就義的年輕愛國詩人。唸裴多菲詩句,回憶起中學教科書上寫「意映卿卿如晤」〈訣別書〉的林覺民,不由得心頭泛起一陣熱潮。
那日離開秀明路公寓,心裡反覆盤桓著裴多菲詩句,恍然間,我彷彿明白潛藏在尉大哥漫長追尋中心靈的祕密——原來,大哥從來都是個根深蒂固的浪漫主義者呀!
生命、愛情、自由。走著走著,我變得年輕了。
奚淞於二○一九年四月新店溪畔微笑堂
文章試閱
〈到梵林墩去的人〉
小火車站上,一個年輕人正敲打著售票的窗口。
「買票!買票!」他沙啞地叫著,深沉地望首四周。下午的陽光慵倦地照在街上,一陣黃沙忽忽地捲過去,一個光腳的小男孩正穿過那裡,跑進那間半掩的店鋪。車站裡垂敗下來的木梁上,一隻叫不出名字的黑甲蟲在靜靜地貼伏著。
「買票!」他又重敲著售票的窗口。沒有人答應。他搖搖頭,很滑稽地用手摸著屁股。
「他媽的,沒有人。」他喃喃著:「人都死光了。——呃,買票。」
「唔!唔!」一個蒼老的聲音隔著窗子響著:「是你嗎?透西?」
「透西個屁!買票。」
「透西,你不該忘記給老人家送飯的。」
「誰要給你送飯,快點,我要買一張車票。」
「你不是透西嗎?」窗口打開了:「透西愈來愈野了。你下次該對他說不要忘記給老人家送飯。」
「你睡著了?」
「是你要一張車票嗎?」
「還有誰呢?」
「你不該來得這麼早。」
「早麼?」
「車子要三個鐘頭以後才來。」
「三個鐘頭?」
「三個鐘頭零二十七分。」
「他媽的,你們不能多開一班車子?」
他摸著口袋,把一張皺了的票子遞過去:
「給我一張到梵林墩的車票。」
「梵林墩?」
「呃,梵林墩!」
「沒有到梵林墩的車子。」
「那我該坐哪一班呢?」
「我不知道,我沒聽說過這個地方。」
「沒有人到過梵林墩嗎?」
「沒有人到過。」
「他們都到哪裡去?」
「最遠他們到過農門鎮。」
「哪一個農門鎮?」
「就是那個農門鎮。尤烈說,那裡的風,柔柔的,那是打海上吹來的。我記得清清楚楚的,他說過,得讓這裡的風也變得柔柔的,那時候他剛回來,我們攀著肩膀在街上走,風沙吹在他的臉上灰黃灰黃的。」
「他不該回到這裡,鬼才喜歡這個地方。」
「你不該這樣說,這是塊最好的土地。」
「你去住吧,給我張梵林墩的車票。」
「沒有到梵林墩的車票,它只開到農門鎮。」
「就買到農門鎮——。這真是個鬼才住得下去的地方。一群豬,沒有人知道梵林墩的名字。」
「這是你的車票,你可以回去睡覺了。」
「我為甚麼要回去睡覺?我已經買好了車票。」
「你該再睡一會,車子來還要三個多鐘頭。」
「它不能早到些嗎?」
「你可以回去再推兩班車子。」
「推甚麼車子?」
「你不是在礦場推煤車嗎?」
「甚麼礦場?」
「你該再去看看。尤烈說,那會是天下最大的礦場。」
「我不要去看,我要看它幹甚麼?」
「你該回去再推兩班車子。」
「沒有甚麼人叫我推煤車,這是天下最壞的地方。」
「那你每天都幹甚麼呢?」
「我記不得自己都幹些甚麼,好像是昨天的事,山苟伯叫我洗過一落盤子。」
「那你可以回去再洗一落盤子,太陽下山的時候,你才能聽見火車的叫聲。」
「我不想去洗甚麼盤子,山苟伯說:年輕人該到梵林墩去。——你們不能多加一班車子嗎?我要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
「你可以到那邊去等,透西真是玩野了,你該對他說不該把老人家的飯忘記。」
「誰是透西?」
「他一定又去抓斑鳩去了,他爸爸就喜歡抓斑鳩,老胡子墳上那棵桑樹上每年都有一窩最好的斑鳩,你該嚐嚐那棵樹上的桑葚,那是熟得發紅發紅的葚子。」
「我不想吃甚麼桑葚,我要到梵林墩去——為甚麼你們不安張椅子?」
「問塔基跟麻撒就知道了。」
「誰是塔基跟麻撒?」
「第二個礦坑的兩個傢伙。」
「我不認識塔基,也不知道誰是麻撒。」
「你不是在礦場推煤車嗎?」
「沒有誰要我去推煤車。」
「那你可以去問尤烈。」
「誰是尤烈?」
「你沒有賭過錢嗎?」
「我沒有賭過。」
「你該到尤烈那裡碰碰運氣。」
「我根本不認識誰是尤烈,我也不想碰甚麼鬼運氣,我只想有張椅子歇歇腳。」
「我該去罵塔基跟麻撒,他們真不該喝得爛醉。」
「他們喝得醉不醉,管我個屁事。」
「塔基醉的最兇,是他先把椅子拆散的。」
「你不能再添一張椅子嗎?」
「我找不到黎坤。」
「誰是黎坤?」
「你不是在礦場推煤車嗎?」
「誰去推煤車呢?這是個鬼也要餓瘦的窮地方。」
「你該到尤烈那裡去看看黎坤。」
「我不認識誰是尤烈,我也不知道誰是黎坤。」
「你該到尤烈那裡碰碰運氣,你可以跟黎坤喝兩杯。」
「我不想跟誰喝一杯,他們罵人的話跟豬叫一樣。山苟伯說:你不該躲在屋角裡一個人哭,你該到梵林墩去。我要離開這個地方,我不要去認識甚麼尤烈或黎坤。」
「你該去見見黎坤,他總坐在那裡。哈,好小子!他總會先叫你。」
「他為甚麼要叫我呢?我已經不欠誰的,誰也不能再把我踢醒。」
「他會喜歡你——跟我來小伙子,他會對你說,我要讓這裡的風變得柔柔的。」
「沒有甚麼地方的風像梵林墩的那樣柔,農門鎮的也沒有。——你們的車子還不如換個牛車,一群笨豬。」
「你該先去看看黎坤,他會告訴你水壩築在哪裡。」
「誰的水壩築在哪裡?」
「你不認識羅予六嗎?他可以帶你去。」
「他帶我去梵林墩嗎?他不會知道的,而且我根本不認識誰是羅予六。」
「爬過那座山頭你就可以找到他。」
「我為甚麼要爬過那個山頭?」
「你該去的,那樣你就可以看見那座茅屋。」
「我耍到梵林墩去,我不要甚麼茅屋。」
「你可以走過去,羅予六的來西會先招呼你。」
「誰是來西?」
「那是羅予六餵的黑狗,你不知道牠多靈巧,有一次他替透西的爸爸捉到一隻山兔,透西說,來西是羅予六的女兒。」
「誰要見羅予六幹甚麼?」
「他會先帶你看他種的玉米。」
「這是個鬼也要餓瘦的地方,沒有誰帶你去看玉米。」
「看過玉米,他會帶你去看他抓來的山雞。」
「我要趕到梵林墩好好睡一覺,你不知道這個鬼地方連睡覺也會有人把你踢醒,到梵林墩我要先睡一覺,我不想看甚麼山雞。」
「羅予六的板煙最夠味了,你該先嚐一嚐。」
「我不要抽甚麼煙。」
「那你該嚐嚐那些野果子,他會給你找兩顆又紅又甜的,你該選一個青的嚐嚐,你該嚼嚼那種酸味。」
「我甚麼也不要,我要趕快離開這個鬼地方。——你們這是哪國的屁火車,太陽快要落了,要等到哪一年它才會開來呢?」
「這時候那個山頭最好看了,你該站在那塊大青石上往下望一望。」
「我為甚麼要去那個山頭,我的票已經買好了,我要到梵林墩去。」
「羅予六會跟你說水壩怎麼做。」
「甚麼水壩?」
「黎坤的水壩,他說等水壩好了,我們就有最柔最柔的風。你不知道他多喜歡摸別人的頭,他說:好小子,那時候你可以好好地泡在水裡洗一洗身上的煤煙。」
「我要到梵林墩好好洗一洗身上的爛泥,再沒有一個地方比這裡的街道更髒,你們真該在路上養一群豬!」
「黎坤會把這條街整治得好好的,他說:小伙子,我們先該把街道鋪上瀝青,很多人會到我們這裡來。」
「只有倒霉倒到家的人才會到這個鬼地方來,只有天下第一號窩囊廢才住得下去。」
「他們會來的,你該到尤烈那裡去。」
「我去找他幹甚麼?我根本不認識誰叫尤烈。」
「他會告訴你那些礦苗在哪裡。你不知道,那一晚他們醉得多兇,黎坤抓著那塊石頭笑得像個瘋子,尤烈不該,那晚他吐了黎坤一身。」
「誰要看那些石頭,普天之下再找不到這麼討厭的石頭,它只能拿來敲你的腦袋,我一輩子也忘不了那個最討厭的黑傢伙,下一次我一定要敲掉他那兩顆黃板牙。——你這裡連水也沒有嗎?」
「你口渴嗎?你該罵罵透西,他不該這樣忘掉老人家。」
「我不知道誰叫透西,你不能去找他嗎?」
「等我找到他了,我一定要先敲敲他的腦袋。黎坤會把老呂西找來,那樣我就可以敲透西的腦袋了。」
「誰是老呂西?」
「黎坤說,他要在街東頭那塊地上蓋一座閣樓,好小子,你病了嗎?找老呂西去吧,好好地聽他的話。」
「你該先去找一罐水來,要不然再沒有誰能去見老呂西了。」
「透西一定野到山裡去了,真該有人告訴他不該忘記老人家。」
黃昏漸濃了,燃紅的晚雲把街道映得分外悠長,在餘暉中,老人家一跛一跛地向街道走去。
「他媽的,沒有人要來的地方,火車司機一定他媽的睡著了。」
街道上忽然出現四個人。
「一定在這裡。」一個黑色的傢伙叫著,那兩顆門牙向外敞露著。
「這不是嗎?」
「你們還要幹甚麼?」年輕人說。
「跟我們回去。」
「我已不欠你們甚麼,沒有人能叫我做甚麼。」
「你要溜嗎?」
四個人漸漸圍攏過來:
「乖乖地跟我們回去,不然要你的狗命。」
「回去幹甚麼?」
「跟我們去見杜老大。」
「去見那豬玀嗎?吃屎的傢伙。」
「走!」
天漸漸暗了。老人微喘著走了進來。
「該有人跟黎坤說,街道也沒人管了,晚上也沒有燈了,要是尤烈喝醉了,他一定會被拌倒。黎坤到哪裡去了呢?他說就要回來,帶老呂西一起來,他買的是農門鎮的車票,但是阿朱、第松都沒有找到他。該有人跟他說,礦石上已經長滿青苔了,水壩上的野草也愈來愈長了。透西愈來愈野,麻撒的醉酒也更加厲害了。他們到哪裡去了呢?尤烈也不見了。椅子該修了,該有人告訴他們,但是,她們在哪裡呢?農門鎮沒有他們,到底他們去了哪裡?——也許他們到梵林墩去了。」
他一跛一跛地走來,對著月台叫喊著:
「喂!年輕人!」
「喂!你跑到哪裡去了?車子就要來了,要是你見到黎坤,你該告訴他這裡的一切。」
「喂!」他叫著。
「喂!年輕人!」他叫著:「你不是口渴嗎?水已經來了,車子就要進站了……」
不遠的地方火車在晚空中寂寞地嘶喊著。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