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斜陽:幻滅中的溫柔革命,太宰治女性獨白經典名作【另收錄〈女人的決鬥〉,女人一旦戀愛就完了。別人只能束手旁觀】
| 作者: |
太宰治
|
| 譯者: |
劉子倩 |
| 書城編號: |
1583286 |
原價:
HK$117.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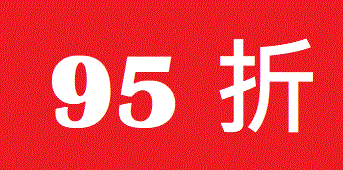
現售:
HK$111.15
節省:
HK$5.85 購買此書 10本或以上 9折, 60本或以上 8折
購買後立即進貨, 約需 7-12 天
|
| |
|
|
| |
|
|
出版社: |
大牌
|
| 出版日期: |
2019/07 |
| 頁數: |
288 |
| 尺寸: |
14.8x20x1.9 |
| ISBN: |
9789867645777 |
|
|
商品簡介 |
愛情沒有理由。過了悲哀的極限後,
那種不可思議的微明心境如果就是幸福感……
所謂的幸福感,
或許就像是沉在悲哀的河底,微微閃爍的沙金吧。
「《斜陽》將會是我從未寫過,最美麗的紀念小說。」──太宰治
雨後出現晴空的彩虹,終將縹緲消失,
可是掛在心頭的彩虹,似乎永無消散之日。
《斜陽》以情人太田靜子的日記為創作藍本,為太宰晚期代表作,更是破滅美學的登峰之作。太宰以細膩深刻的女性視角,描述在混亂、新舊價值衝突的戰後社會,貴族的沒落與失落,文中更傳達對殘缺、消逝之美的嚮往──「破壞,既哀傷又可悲,同時也很美。」
書中不同人物在幻滅擺盪中的不同選擇,也引導出相異的生活處境與命運走向。其中女主角和子為愛與革命奮鬥的篤定與堅忍,展現出高度的存在自覺,重新銘刻了生命的意義,也讓她從生命的旁觀者轉向實踐者。
「透過基本上無修改、猶如一氣呵成寫出來的強而有力文字,顯示出太宰對《斜陽》的強烈意志。」──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中島國彥
那是犧牲者的臉孔。尊貴的犧牲者。
我的人。我的彩虹。My child。可惡的人。狡猾的人。
我悲傷又悲傷的愛情終於實現。
《斜陽》由四個關鍵人物──「最後的貴族」母親、姊姊和子、弟弟直治,以及直治的文學老師上原構成,他們各自在精神荒廢的戰後社會,摸索、傾訴自己的價值與生存之道──
即使優渥輝煌的富裕生活已成為蒼茫迷離的過眼雲煙,身為「真正的貴族」的母親,仍優雅順從地接受命運;藥物中毒、極端頹廢的直治──「我這樣一棵小草,在這世間的空氣與陽光中,活得很艱難。」則是在日益頹喪中,選擇以自戕逃離;上原與直治同樣過著靡爛的生活,但前者卻是在底層階級中,隨波逐流、歡愉的墮落;姊姊和子則能懷抱純粹,在「愛與革命」的戰鬥中,封存被現實齧咬的痕跡,自黑暗深處迎向犧牲者的黎明。
*特別收錄〈女人的決鬥〉──「女人一旦戀愛就完了。別人只能束手旁觀。」
「這段期間我也有種種回憶,並且將自身經歷的感懷,不讓讀者察覺地悄悄融入故事的最底層,所以於我個人而言,我想將來這或許會成為我深愛的作品之一。」──太宰治
〈女人的決鬥〉,是太宰仿擬創作、評論森鷗外的同名譯作(原為德國劇作家歐連伯之作,日譯本由森鷗外譯介),展現女人的道德革命,為太宰自述「至少做了一點新嘗試」的翻案代表作,也是太宰個人生涯中,相對幸福安定時期的創作。「女人並不像玩具、蘆筍、花園那麼簡單。……女人的真實,根本無法寫成小說。」文中撲朔迷離的敘述者、對於女性心理鞭辟入裡的刻畫,再次印證太宰治超越世代的文學魅力。
作者簡介
太宰治
本名津島修治,出生於青森縣北津輕郡金木町的知名仕紳之家,其父為貴族院議員。
1930年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就讀,師從井伏鱒二,卻因傾心左翼運動而怠惰學業,終致遭革除學籍。1933年開始用太宰治為筆名寫作。1935年以短篇《逆行》入選第一屆芥川賞決選名單。並於1939年以《女生徒》獲第四屆北村透谷獎。但始終與他最想贏得的芥川賞無緣。
太宰治出生豪門,卻從未享受到來自財富或權勢的種種好處,一生立志文學,曾參加左翼運動,又酗酒、殉情,終其一生處於希望與悔恨的矛盾之中。在他短暫的三十九年生命中,創作三十多部小說,包括《晚年》、《二十世紀旗手》、《維榮之妻》、《斜陽》、《人間失格》等。曾五次自殺,最後於1948年和仰慕他的女讀者於東京三鷹玉川上水投河自盡,結束其人生苦旅。
譯者簡介
劉子倩
政治大學社會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社會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有小說、勵志、實用、藝術等多種書籍,包括三島由紀夫《憂國》、川端康成《伊豆之旅》、谷崎潤一郎《春琴抄》、太宰治《女生徒》、夏目漱石《門》等日本文學作品。
書籍目錄
斜陽
女人的決鬥
文章試閱
四
到底該不該寫信,我遲疑良久。然而,今早我驀然想起耶穌說的那句「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遂奇妙地有了勇氣,終於決定寫這封信。我是直治的姊姊。您或許忘了?如果忘了,請回想一下。
直治最近又去打擾您,似乎承蒙您照顧,真是不好意思。(不過,其實直治愛怎麼做是直治的自由,我替他出頭道歉好像也有點荒謬。)今天不是為了直治,而是為了我自己的事拜託您。我聽直治說您位於京橋的公寓受災,之後搬到了現在的住處,本來想去您東京郊外的府上拜訪,但家母最近又有點身體欠佳,實在無法扔下家母獨自去東京,所以只能以寫信的方式請託。
我有事與您相商。
我要商量的事,就以往的「女大學」的立場看來,或許非常狡猾、卑劣,甚至是惡質犯罪,但我,不,我們,若繼續這樣實在活不下去,所以我想請弟弟直治最尊敬的您,聽聽我真誠無偽的想法,請您給我一點建議。
我已經受不了現在的生活了。不是喜歡或討厭的問題,是這樣下去我們母子三人根本活不了。
昨天也很痛苦,渾身發熱,喘不過氣,不知該拿自己怎麼辦,結果中午過後,下面農家的姑娘冒雨扛了米送來。我則按照約定拿我的衣服交換。姑娘在餐廳和我面對面坐著喝茶,同時用非常實際的口吻說:
「小姐,您光靠賣東西,今後還能維持多久的生活?」
「一年半載吧。」
我回答,用右手半遮住臉說,
「我想睡覺。很睏,睏得不得了。」
「您是累壞了啦。大概是神經衰弱才會想睡覺。」
「或許吧。」
我幾乎落淚,心頭驀然浮現現實主義這個字眼,以及浪漫主義這個字眼。我沒有現實主義。現在這樣,活得下去嗎?這麼一想,頓感全身發冷。母親似乎已半是病人,臥床休養時好時壞,弟弟也如您所知心裡病得很重,他在家時,為了喝燒酒,經常跑去附近的旅館和餐館,每三天就拿我們賣衣服換來的錢去東京揮霍一趟。可是讓我痛苦的不是這種事。我只是害怕,那讓我清楚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在這樣的日常生活中,就像芭蕉葉沒有散落便逐漸腐爛一樣,就這麼佇立著自動腐敗消散。我真的受不了了。所以我寧可違抗「女大學」的訓誡,也要逃離現在的生活。
因此,我想找您商量。
現在,我想明確對母親和弟弟宣言。我想明白對他們說,我老早就愛上某人,將來,我打算成為那個人的情婦。那個人,想必您也已經知道了。那人的姓名縮寫是M.C。打從之前,每當發生痛苦的事,我就想飛奔去M.C的懷抱,滿腔相思痴狂欲死。
M.C和您一樣已有妻小。此外,似乎也有比我更年輕貌美的女性友人。然而,除了投奔M.C,我覺得我已別無生存之道。我還沒見過M.C的妻子,但我聽說他的妻子似乎非常溫柔賢慧。想到他的妻子,我就覺得自己是個可怕的女人。然我現在的生活,比那個更可怕,讓我無法打消投奔M.C的念頭。我想馴良像鴿子、靈巧像蛇地實現我的戀情。不過,想必母親、弟弟,乃至世人都不會贊成我的想法吧。不知您認為如何?到頭來,我除了獨自思考獨自行動別無選擇,想到這裡,我又流淚了。因為這是有生以來頭一遭的事情。這個艱難的選擇,難道就無法取得周遭眾人的祝福嗎?我彷彿要思考甚麼複雜代數的因數分解的解答,絞盡腦汁,漸漸覺得好像有一個突破口足以輕鬆漂亮地解開難題,甚至忽然變得很快活。
不過,重點是M.C本人對我是甚麼態度。想到這裡,我就很洩氣。說穿了,我是一廂情願倒貼……該怎麼說呢?我甚至不能算是倒貼的老婆,只能算是倒貼的情婦?因此,如果M.C那邊堅持不肯,我也沒輒了。所以我想請求您。能否替我問問他的想法?六年前的某一天,我的心頭出現一抹淡淡的彩虹,那雖然不是戀慕也不是愛情,但隨著歲月累積,那道彩虹增添了鮮明色彩,到目前為止,我總是能一眼就看見它。雨後出現晴空的彩虹,終將縹緲消失,可是掛在心頭的彩虹,似乎永無消散之日。拜託,請幫我問問他的意思。問他到底是怎麼看待我的。或者,他覺得我就像雨後天空的彩虹?甚至,早已消失無蹤?
若真是那樣,我也必須抹消我心頭的彩虹。然而除非先抹消我的生命,否則我心頭的彩虹恐怕難以消失。
祈求您的回音。
謹致 上原二郎先生(我的契訶夫。My Chekhov。M.C)
……
六
那天是個刮著強烈寒風的日子。在荻窪車站下車時,天色已經昏暗,我攔下路過的行人,說出那人的地址,請教該往哪個方向走,在昏暗的郊外路上徘徊了將近一小時,徬徨無助的我不由落淚,後來我在碎石子路上絆了一跤,木屐的鞋帶斷了,我呆立原地不知如何是好,驀然發現右手邊二棟大雜院其中一戶的門牌,即便在黑夜中也白濛濛地浮現,上面好像就寫著「上原」,我一腳只穿著足袋,就這麼奔向那家的玄關,再仔細一看門牌,的確寫著「上原二郎」,但屋內一片漆黑。
怎麼辦?我當下又愣住了,之後,我抱著豁出去的心情,整個人撲倒在玄關的格子門上,
「有人在嗎?」
我說,雙手的指尖撫摸門上的木條,一邊小聲囁嚅:
「上原先生。」
竟然有人回應。不過,是女人的聲音。
玄關門從內拉開,一個臉孔瘦小帶有古典氣質、好像比我大三、四歲的女人,站在玄關的黑暗中倏然一笑,
「請問是哪位?」
女人問話的語調,毫無惡意或防備。
「我是,那個……」
可我忽然遲疑,不敢說出自己的名字。唯獨在此人面前,我的滿腔愛慕,奇妙地感到心虛。我戰戰兢兢,幾乎是卑微地說:
「請問老師呢?不在嗎?」
「是。」
女人回答,憐憫地看著我的臉,
「不過,他的去處,大致猜得出來……」
「很遠嗎?」
「不會。」
女人彷彿覺得很好笑地抬起一隻手掩嘴,
「就在荻窪。您如果去車站前那家白石關東煮,多半可以打聽到他的下落。」
我迫不及待就想走,
「啊,這樣子嗎。」
「哎呀,您的木屐。」
在她的邀請下,我走進玄關,坐在低矮的台階上。上原太太拿給我的,大概叫做簡易鞋帶,是鞋帶斷掉時可以簡單修繕的皮繩,在我修理木屐之際,上原太太點燃蠟燭拿來玄關,一邊還態度悠然地笑著說:
「不巧家裡二個燈泡都壞了,最近燈泡不僅貴得嚇人還很容易壞,真是糟糕,如果外子在還可以叫他去買,可是昨晚和前晚他都沒回來,所以我們已經連續三晚一毛錢也沒有被迫提早就寢了。」
上原太太的身後,還站著一個年約十二、三歲,眼睛很大,看起來從不輕易接近外人的纖細女孩。
敵人。我不願這麼想,然而,這對母女遲早肯定會把我當成敵人憎恨我。想到這裡,我的戀慕一時之間好像也冷卻了,我換好木屐的鞋帶,站起來拍掌撢去雙手的灰塵,同時有種淒涼猛然湧上全身令我難以忍受。我的心情激盪,很想立刻衝上屋內,在黑暗中抓著上原太太的手嚎啕大哭,但是驀然間,我想到哭完之後自己沒台階可下的可悲模樣,頓時厭煩地打消念頭,
「謝謝您。」
我格外客氣地致謝,走出門外,被冷風吹拂,戰鬥開始,戀慕,喜歡,痴情相思,真的戀慕,真的喜歡,真的痴情相思,因為戀慕所以沒法子,因為喜歡所以沒法子,因為痴情相思所以沒法子,那位太太的確是罕見的好女人,那位小女孩也很漂亮,可我就算被拉到神的審判台前,也絲毫不覺得自己有錯。人,本就是為了愛情與革命而誕生,神應該也不可能為此降下懲罰,我完全沒錯,是真的喜歡所以理直氣壯,縱使為了見他一面必須連續兩、三晚露宿野地,也必然堅持到底。
|
|
|
|
|
|